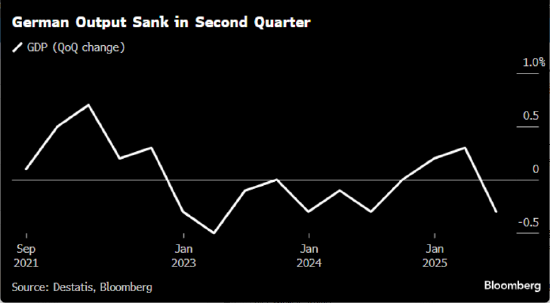一九八三年的夏天,热得能把人烤出油来。我蹲在瓜棚里,摇着蒲扇,汗水还是顺着脊梁骨往下淌。二十岁的年纪,家里种了二十亩西瓜,爹说今年收成好,能卖个好价钱,让我夜里守着优配配件助手,怕有人偷。
"柱子,你可警醒着点。"爹临走前叮嘱我,"咱家这瓜可金贵着呢。"
"知道了爹。"我应着,心里却想着别的事。
我叫周平,村里人都叫我柱子,因为我小时候长得壮实。我家在村东头,离河不远,西瓜地就在河边那片沙土地上。这地方种出来的瓜特别甜,瓤红籽黑,咬一口能甜到心里去。
天渐渐黑了,蝉鸣声也歇了,只剩下田里的蛙叫和偶尔的虫鸣。我躺在瓜棚的草席上,枕着手臂,望着棚顶漏进来的星星。这瓜棚是爹和我在开春时搭的,四根杨木柱子,顶上铺着芦苇席,三面围了高粱秆,留一面进出。
睡不着,我就想起萍儿。萍儿姓李,叫李萍,住在村西头,比我小一岁。我们从小一块长大,她总跟在我屁股后头"柱子哥柱子哥"地叫。记得小时候在河边摸鱼,她穿着小花褂子,裤腿卷到膝盖上,白生生的小腿在阳光下晃眼。我抓了鱼,她就拍着手笑,眼睛弯成月牙。
展开剩余91%后来我们都长大了,见面反而少了。她爹在县城供销社上班,家里条件比我们好,送她去读了初中。我小学毕业就在家帮爹种地。去年冬天,听说她爹给她说了门亲事,是县城一个干部的儿子。我听到这消息时,正在地里砍白菜,手里的镰刀差点砍到自己的脚。
"萍儿要嫁人了..."这念头在我心里转了好几个月,像根刺,拔不出来也咽不下去。
我翻了个身,草席沙沙响。夜风吹进来,带着泥土和瓜叶的清香。远处传来几声狗叫,然后又归于寂静。
不知什么时候睡着的,突然一声炸雷把我惊醒。我猛地坐起来,外面已经下起了雨,雨点打在瓜叶上噼啪作响。就在这时,我发现身边多了个人。
"谁?"我吓了一跳,伸手去摸放在旁边的铁锹。
"柱子哥,是我..."
这声音我听了十几年,闭着眼都能认出来。是萍儿。
闪电划过,照亮了瓜棚。萍儿就坐在我旁边,头发湿漉漉地贴在脸上,身上的碎花衬衫也湿了大半,紧紧贴在身上。她的眼睛在黑暗里亮晶晶的,像是含着泪。
"萍儿?你怎么在这儿?"我的心跳得厉害,手都不知道往哪儿放。
她没说话,只是往我这边靠了靠。雨下得更大了,打在棚顶上像敲鼓。我能闻到她身上淡淡的雪花膏香味,混着雨水的清新。
"我...我听说你在这儿守夜。"她声音很小,几乎被雨声淹没,"就想来看看你。"
我喉咙发紧,不知道该说什么。我们从小玩到大,可自从她上了初中,见面就少了。偶尔在村里碰到,也只是点点头,连话都说不上几句。
"你爹知道你来这儿吗?"我终于憋出一句。
她摇摇头,头发上的水珠甩到我脸上,凉凉的。
"柱子哥,我..."她突然抓住我的手,"我喜欢你。"
这句话像另一道闪电,把我劈得外焦里嫩。我的手被她握着,能感觉到她在发抖,不知道是冷的还是紧张的。
"萍儿,你别开玩笑..."我结结巴巴地说,想把手抽回来,又舍不得。
"我没开玩笑。"她声音大了起来,"从小我就喜欢你,可你从来不说。我爹给我说亲,我...我不想嫁别人。"
雨更大了,风把雨点斜着吹进瓜棚,打在我们身上。萍儿的脸上湿漉漉的,分不清是雨水还是泪水。
"你爹给你说的那门亲事..."我艰难地开口。
"我不要!"她突然扑进我怀里,把我撞得往后一仰,"柱子哥,我只要你。我知道你家穷,我不在乎。我们一起种西瓜,日子会好的..."
她的身体在我怀里颤抖,我能感觉到她急促的呼吸和快速的心跳。我的脑子一片空白,只有她的话在耳边回响。
"萍儿..."我终于鼓起勇气,伸手抱住她,"我也喜欢你,从小就喜欢。可我...我配不上你。"
"胡说!"她抬起头,在闪电的光亮中,我看到她红红的眼睛和倔强的嘴角,"你比谁都好。你记得吗,小时候我掉河里,是你跳下去救的我。从那天起,我就决定要嫁给你。"
我当然记得。那年萍儿八岁,在河边洗衣服不小心滑进深水区。我正好在附近放牛,听见呼救就跳了下去。水很急,我差点也被冲走,最后硬是拽着她的辫子把她拉了上来。为此她娘还给我家送了一篮子鸡蛋。
"可你爹..."
"我会说服他的。"萍儿坚定地说,"只要你愿意要我。"
雨声中,我听见自己心跳如雷。怀里的姑娘是我从小喜欢到大的,现在她就在我怀里,说她要嫁给我。我突然觉得,什么穷啊富啊,都不重要了。
"萍儿,"我捧起她的脸,"如果你真的愿意跟我过苦日子,我...我这辈子一定对你好。"
她笑了,眼泪却流得更凶。我笨拙地用袖子给她擦脸,却越擦越湿。雷声隆隆,雨点敲打着瓜叶,像是天地在为我们奏乐。
"柱子哥,我们逃吧。"她突然说,"去城里打工,等生米煮成熟饭再回来。"
我吓了一跳:"那怎么行!你爹会打断我的腿优配配件助手。"
"我不管。"她任性地说,像小时候要不到糖时的样子,"反正我就要跟你在一起。"
我看着她倔强的样子,心里又酸又甜。这个傻姑娘,为了我连私奔都想出来了。我摸摸她的头发,湿漉漉的,像摸着一匹绸缎。
"萍儿,我们不能跑。"我轻声说,"我要堂堂正正地娶你。明天我就去找你爹提亲。"
"真的?"她眼睛一亮,随即又暗下来,"可我家要的彩礼..."
"我会想办法。"我握紧她的手,"今年西瓜收成好,卖了钱应该够彩礼。不够的话,我去借。"
她靠在我胸前,小声说:"柱子哥,我等你。"
雨渐渐小了,只剩下滴滴答答的声音。萍儿在我怀里睡着了,呼吸均匀。我轻轻拍着她的背,像哄小孩一样。天快亮的时候,雨停了,东方泛起鱼肚白。
我看着怀里熟睡的萍儿,心里满满的都是幸福和决心。不管多难,我都要娶这个姑娘。她是我的青梅竹马,是我从小守护到大的宝贝,我不能让她嫁给别人。
晨光中,我轻轻吻了吻她的额头,许下了一个庄稼汉最朴实的承诺:"萍儿,这辈子我一定让你过上好日子。"
天刚蒙蒙亮,萍儿就醒了。她揉了揉眼睛,看到我正盯着她看,脸一下子红到了耳根。
"柱子哥...我该回去了。"她坐起身,整理着皱巴巴的衣裳,"我娘该找我了。"
我点点头,心里有千言万语,却只憋出一句:"路上小心。"
萍儿走到瓜棚口,又折返回来,飞快地在我脸上亲了一下:"记住你说的话。"然后就像只受惊的兔子一样跑走了,只留下田埂上一串湿漉漉的脚印。
我摸着脸上被她亲过的地方,那里烫得像被火燎过。太阳升起来了,照在西瓜地上,昨夜的雨水在瓜叶上闪着光。我摘了个熟透的西瓜,一拳砸开,鲜红的瓜瓤让我想起萍儿害羞时的脸蛋。
回到家,爹正在磨镰刀。我把萍儿的事跟他说了,他的眉头皱成了疙瘩。
"柱子,李家那门槛,咱跨得过去吗?"爹叹了口气,"他爹在供销社当干部,眼睛长在头顶上。"
"爹,我想试试。"我蹲在地上,手指抠着泥土,"萍儿说她愿意等我。"
爹把镰刀往磨石上一放:"行,爹支持你。明天我找王媒婆去提亲。"
第二天,王媒婆穿着她最好的蓝布褂子去了李家。不到一袋烟的工夫就回来了,脸色难看得很。
"李家说了,"王媒婆撇着嘴学舌,"'周家那穷酸样,也敢来提亲?癞蛤蟆想吃天鹅肉!除非拿出三千块彩礼,否则免谈!'"
三千块!我惊得手里的水瓢都掉了。那时候,一个壮劳力一年到头也攒不下三百块。三千块,我得攒十年!
爹蹲在门槛上抽旱烟,一言不发。我知道他为难——娘走得早,家里就我们爷俩,这些年勉强糊口,哪有什么积蓄。
"爹,我想好了。"我握紧拳头,"今年西瓜卖了钱,我去城里打工。三千块,我一定能挣到!"
爹吐出一口烟,点点头:"去吧,家里地有我。"
接下来的日子,我像头不知疲倦的牛,整天泡在西瓜地里。除草、施肥、翻藤,每一棵瓜苗都是我的希望。有时候半夜醒来,我会跑到地里,借着月光看着那些圆滚滚的西瓜,想象它们变成一沓沓钞票,铺就我娶萍儿的路。
萍儿也没闲着。她偷偷托人给我捎信,说她在县供销社帮我问了,今年西瓜收购价能到一毛五一斤。要是二十亩地都丰收,能卖将近两千块。
七月底,西瓜熟了。我摘了一个又一个,堆在田头像小山。萍儿说的没错,供销社的收购员来看过,说我们的瓜品相好,答应全要了。
就在装车那天,村里出了事。张寡妇家的小儿子在河边玩水,被急流冲走了。我正扛着西瓜,听见呼救声,想都没想就跳进了河里。
那水流得急,我在水里扑腾了半天,终于抓住了那孩子的衣领。上岸时,我的腿被水底的碎玻璃划了道大口子,血把河水都染红了。
张寡妇抱着孩子哭成了泪人,非要给我磕头。我没当回事,随便包了伤口就继续装车。没想到这事传得飞快,第二天,村里人都叫我"救人英雄"。
更没想到的是,萍儿爹竟然上门了。
那是个闷热的下午,我正在院子里修补装西瓜的筐子,抬头看见一个穿着白衬衫、梳着背头的中年男人站在我家篱笆外。我愣了好一会儿才认出是萍儿爹——以前他见了我都当没看见,今天居然登门了。
"周平啊,"他站在院子里,手背在身后,"听说你救了张家小子?"
我赶紧站起来,裤子上还沾着筐子的篾条:"李叔,您坐。就是碰巧..."
他没坐,只是上下打量我:"你腿上的伤怎么样了?"
"没事,小口子。"我有点受宠若惊。
萍儿爹从兜里掏出两张大团结放在桌上:"买点补品。年轻人,见义勇为是好事。"
他走后,我捏着那二十块钱,半天没回过神来。爹从地里回来,听说这事,眼睛一亮:"柱子,有门儿!"
果然,没过几天,王媒婆又去了李家,这次带回了不一样的消息。
"李家松口了!"王媒婆拍着大腿说,"彩礼降到一千五,但要三转一响,还要办十桌酒席!"
三转一响——自行车、缝纫机、手表和收音机,这在当时是城里人结婚的标配。对我们庄稼人来说,简直是天文数字。
"爹,咱们..."我看向爹。
爹把烟锅在鞋底上磕了磕:"娶!砸锅卖铁也娶!"
西瓜卖了钱,加上爹这些年攒的,还差一大截。我决定去县城打工。临走前一天晚上,萍儿偷偷跑来送我。
月光下,她塞给我一个手绢包着的东西。我打开一看,是一块上海牌手表,表链亮闪闪的。
"我攒的零花钱,还有跟同学借的。"她低着头,"你别嫌旧..."
我把表戴在手腕上,心里酸胀得难受。这块表不知道花了她多少心血,表带上有几道划痕,但走得稳稳当当,就像她对我的心。
"萍儿,等我回来。"我握住她的手,"我一定风风光光地娶你。"
在县城,我白天在建筑工地搬砖,晚上去火车站扛包。工棚里热得像蒸笼,蚊子嗡嗡叫,但我一想到萍儿,浑身就有使不完的劲。三个月后,我终于攒够了钱,还多出两百块。
回家那天,我买了辆永久牌自行车,后座上绑着给萍儿买的红绸子衣料。爹看到我黑了瘦了,心疼得直抹眼泪。但看到我带回的东西,又笑得合不拢嘴。
婚礼定在腊月十八,是个黄道吉日。萍儿穿着我买的那身红衣裳,头上插着绒花,美得像画里的人。拜堂时,我紧张得同手同脚,惹得宾客哄堂大笑。
洞房花烛夜,萍儿坐在炕沿上,红烛映着她的侧脸。我轻轻掀开她的红盖头,她抬起眼来看我,眼睛里像有星星在闪。
"柱子哥,我们终于在一起了。"她小声说。
我喉头发紧,只会傻笑:"嗯,在一起了。"
婚后的日子像蜜一样甜。萍儿勤快,把我们家收拾得干干净净。她还在院子里种了月季花,说是要让我们的家像城里一样漂亮。我每天下地回来,老远就能看见炊烟袅袅,知道她在等我。
开春时,萍儿告诉我她怀孕了。我高兴得在地里连翻三个跟头,当晚就去河里摸了条大鲤鱼给她补身子。
然而好景不长。这一年雨水多,西瓜长得不好,价钱也跌了。到了卖瓜的季节,我和爹蹲在地头,看着满地的西瓜发愁——供销社今年只收一半,剩下的得自己想办法。
"柱子,你去趟省城吧。"一天晚上,爹抽着烟说,"听说那边工地工资高。萍儿快生了,处处要花钱。"
我看向正在灯下缝小衣服的萍儿。她低着头,睫毛在脸上投下阴影,没说话,但我知道她听见了。
那晚,我们躺在炕上,萍儿背对着我。我伸手摸她的肩膀,湿漉漉的——她在哭。
"萍儿,我就去几个月。"我扳过她的身子,"等孩子出生前我一定回来。"
她把脸埋在我胸前:"柱子哥,我舍不得你..."
我的心揪成一团,只能更紧地抱住她。
离家那天,萍儿给我装了满满一包袱的干粮和咸菜。她挺着微微隆起的肚子,站在村口的大槐树下送我。我骑出老远,回头还能看见她站在那里,像一棵柔弱但坚韧的小白杨。
在省城的工地,我比在县城时更拼命。白天砌墙,晚上看材料,就为了多挣点加班费。工友们笑我是"钱串子",我不解释,只是每月按时把大部分工资寄回家,只留一点饭钱。
萍儿的信是我最大的慰藉。她不识字,信是找村里会计代写的,但每封最后都会有一个歪歪扭扭的"萍"字,是她自己写的。她说家里一切都好,爹常来帮忙,让我别担心。她说能感觉到孩子在肚子里动,像小鱼在游。她说院子里的月季开花了,红的粉的,等我回来看。
我摸着那些信纸,仿佛能闻到家乡的泥土味和月季的花香,能看见萍儿坐在院子里,阳光透过树叶斑驳地落在她身上。
七个月后,我带着积攒的两千块钱和给萍儿买的新衣裳、给孩子买的拨浪鼓,踏上了回家的路。火车上,我一遍遍想象萍儿见到我时的样子,想象我未出生的孩子是像她还是像我。
当熟悉的村庄出现在视野里时,我的心跳得像擂鼓。远远地,我看见家门口站着个人——是萍儿!她比之前胖了些,肚子已经很明显了。她似乎也看见了我,开始向我跑来。
我扔下行李,张开双臂。萍儿扑进我怀里的那一刻,所有的辛苦都值得了。她身上有阳光和皂角的味道,温暖又踏实。
"柱子哥,"她仰起脸,眼睛里闪着泪光,"咱们的孩子,再有两个月就要来了。"
我轻轻抚摸她的肚子,感受到里面传来的一下有力的踢动。这一刻,我无比确信,无论生活多难,只要我们在一起,就没有过不去的坎。
夕阳西下,我和萍儿手拉手走回家。院里的月季花开得正艳,红的像火,粉的像霞,就像我们的日子,虽然平凡,却充满了希望和色彩。
[全文完]优配配件助手
发布于:河南省易配网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